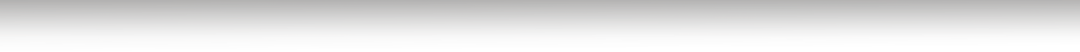
第32章 问罪
梁双树两口和王大奎都没追上梁香梅。
梁香梅一眨眼就没了影儿。
梁香梅跑到哪儿去了呢?
梁香梅哪儿都没去,她转过巷道,跑到跟她相好的瑞子家,梳了头,洗了脸,骑上瑞子家的自行车,向王家窑去了。她要当面向王全天问清楚,为啥要写纸条?王全天到底是咋想的?
就在梁香梅骑着自行车往王全天家赶的时候,田彩云正在王全天家里忙碌着。从王全天被打之后,田彩云除过忙自家地里的活外,还要忙王全天家地里的活,还要照料王全天的日常起居,人家娃是为了她的家事挨了打,自己岂能看着不管?
在田彩云精心照料下,王全天身上的瘀伤平复了,脚腕上的红肿消了,也能下炕了,简单的活儿也能干了,可就是不能用力,稍不注意,裆里的那件物就怪不拉叽的抽着疼,特别是尿尿的时候,疼得王全天两手捂着裆里,额头上就冒汗。
开始的时候,王全天尽量隐忍着,不想让田彩云知道。他想,一个男子汉,让田彩云知道自己的“难言之隐”,实在是丢人害臊得很。可是后来,还是被田彩云发现了。
田彩云悄声问:“咋回事?看你难受得很?”
王全天有些害羞,含含糊糊地说:“老不舒服,尿时疼!”
田彩云有点怕了,悄悄找了娘家当过赤脚医生的刘拐子,把王全天裆里疼的症状详说了一遍,刘拐子听说是让人拿脚踢的疼,也不敢大意,然后跟田彩云到王全天家仔细看了王全天的伤,当着王全天的面,说是不要紧,吃些止疼片就好了,可是背过王全天,却对田彩云说,这病很麻烦,伤了根部的神经,恐怕要影响到性功能了。田彩云急了,问刘拐子有啥办法,刘拐子说,也没啥好办法,只能先开些中药调理着,养着,看情况再说。
其实,刘拐子不说,王全天也能感觉到自己裆里的疼,有些古怪,最明显的就是那物件,不论怎么逗弄,都像死老鼠一样,没一点感觉。王全天很憋气也很恐慌,这些天来,越来越觉得自己已经废了,所以,在痛恨黄料科的同时,也对梁香梅有了看法,明明跟自己谈恋爱,却又跟黄料科搅在一起,弄得自己跟八竿子打不着的黄料科成了怨家对头,这么些天了,连个影子也不见!王全天凭空猜疑梁香梅是脚踏两只船,所以,当王大奎让他写不再纠缠梁香梅的保证书时,他也带有跟梁香梅赌气的意思,三两下就写了。写罢,也觉得不妥,可是也没再深思,因为只要裆里一疼,王全天觉得世间啥事都不重要了,随她去罢,爱弄成啥是啥!
可是田彩云觉得这事麻达了!田彩云是过来人,知道男人裆里的物件对一个男人的重要性,王全天“小弟弟”万一治不好,成了废人,他还娶不娶媳妇?他将过怎样的生活?自己如何面对?田彩云开始后悔让王全天去缑家湾给猪配猪娃去了,自己真是,唉,弄得啥事么!上次王尚世回来,得知王全天被黄料科打了的事,当面没说啥,可从看他的那神情里,分明能看到一丝不满。她不怪老汉,谁家娃为别人家的事让人打了,当家长的都会不满的。田彩云在愧疚之余,暗暗打定主意,无论花多少钱,用啥办法,都要把王全天的病看好,只有这样,她才能心安。所以,天天起来,她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王全天做饭,洗衣服,熬中药,然后才是忙自己家里的事,晚上,也是看着王全天吃了饭,喝了中药,这才回到自己家里去。
这期间,没下巴房宁娃也拧来拧去,跟在她尻子后头,撵到王全天家里谝闲话,她知道,房宁娃肯定是对她和王全天的关系起疑了,可是,她有什么办法能撇清呢!田彩云的确为此苦恼过几天,后来,她想通了,人的嘴是圆的,舌头是扁的,谁爱咋说咋说去,她不能丢下王全天不管,如果那样做了,还能是人吗!
和田彩云一样,王全天心里也重得跟压了一块子石头一样。他本来想把黄料科打他的真实原因说给田彩云,又怕田彩云轻看了他,或者认为他是为了减轻她的思想负担才这样说,所以就一直憋着。后来,他想把王大奎游说放弃和梁香梅谈恋爱的事告诉田彩云,让田彩云知道王大奎回来又不见她后,不知道又要惹出什么事来,所以就来了个闷不做声。可又担心万一田彩云知道王大奎回来过,问为啥不告诉她,怎么办呢?一时又想不出自圆其说的办法。想来想去,只好把这些麻缠事憋在了肚子里。
肚子里是搁饭馍的地方,搁了事就饭吃不进去了。田彩云把做的饭端到炕边,王全天没有食欲,没动筷子就端回去了。田彩云的肚子里也愁成了一疙瘩,同样没有搁饭馍的地方。做好的饭菜搁凉了,第二顿又不想热着吃,给两头母猪弄了个好事。
这天,田彩云刚刚给猪喂了食,腾出手来在院子给王全天洗衣服,梁香梅推着自行车进门了。
梁香梅刚进门,看见田彩云,不好意思地说:“走错门了。”调转自行车头往外走。
“你寻谁?”田彩云问。
“我找王全天。”走到门道的梁香梅说。
“没走错门。这就是王全天的家。”田彩云说。
梁香梅心里纳闷:王全天说,家里只有父子两个人,啥时多了一个女人?又扭过自行车头,问:“你是王全天他啥?”
田彩云甩甩手里拧干的内裤,搭在铁丝绳上,不自然地说:“我……我不是他啥,你进来,王全天在房子里。”
梁香梅把自行车靠在院子的树上,走了进去。
一进腰门,梁香梅用眼睛打量了一下,是两对沿的四间低矮的厦子房,一边是两个房子,房子的门窗漆皮斑驳,露出浅灰色木质颜色,门扇有些翘了。糊着窗的报纸发黄,有几个窟窿。一边空着的厦房下,堆放着几件农用家具。天庭沿上压着几个青石条,椽码眼处有两个干马蜂窝。这一切,都铭刻着艰辛岁月的痕迹,穷的程度和王全天说的对上号了,可哪里来的这个当王全天后妈年龄偏小,当王全天媳妇年龄偏大的女人?梁香梅满心疑惑走进了房子。
躺着的王全天听见说话声,坐了起来,还没来得及把自己这一向的疲倦、邋遢、狼狈相整理好,梁香梅进房子了。
王全天挣扎着坐起,有点吃惊地说:“是你?”
一股中药味扑鼻而来,梁香梅扇扇鼻子,几乎惊讶地叫出了声:我的妈呀,这不是我见过的王全天,这分明是从监狱里跑出来的犯人,头发蓬乱,衣领敞开,萎靡不振,炕上的被子窝成一疙瘩。
梁香梅惊疑不安地问:“你这是咋咧些?咋成这样子啦?”说着,在炕墙边的凳子上坐下来。
田彩云笑着端进来两杯水,搁在桌子上,说:“你两个坐,我出去一下。”
田彩云出了房子门,王全天和梁香梅大眼对小眼,闷坐了好一会,王全天才望了一眼冒着热气的杯子,说:“你喝水。”
梁香梅没有去端杯子,问:“刚才那个女人是谁?”
王全天知道梁香梅误会了,连忙说:“我嫂子。”
“你嫂子?”梁香梅奇怪地问:“你咋没说过,哪来的嫂子?”
王全天埋在心里的对梁香梅的不满忽而冒了出来,不耐烦地回了一句:“我堂嫂。你没见过。”
梁香梅有些敏感,语气怪怪地,看着王全天说:“堂嫂?对你挺亲的嘛,连给你把内裤都洗了。”
王全天回避着梁香梅的目光,不吭声。
梁香梅顿了顿,把茶水杯子端给王全天,软声问:“你咋成这样了?发生啥事了?”
王全天不接话,视若无睹,抿着嘴,想了想,恨恨地说:“还不是着了你的祸!”
梁香梅奇怪了,放下茶杯,秀眉紧蹙:“着了我的祸?”
王全天从梁香梅的表情中看出,梁香梅至今还蒙在鼓里,就忍不住把在种猪场里发生的事原原本本的给梁香梅叙说了一遍。梁香梅就像听惊悚故事一样,听得心惊肉跳,目瞪口呆。自己这一段忙养猪场的事,再加上金杏的事,身忙心累,正准备这一段忙过了,好好和王全天商量一下,尽快按乡俗把婚事定下来。没想到这期间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,而且件件与自己有关!梁香梅被黄料科的凶残手段吓住了,原以为黄料科是个不识进退的憨货,黄料科的父亲黄西亮做事有些霸道,万万没想到这父子俩竟然软硬兼施,就像死蛇一样,硬要缠到自己这棵树上来。所以,听了王全天的叙说,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王全天见梁香梅不说话,以为梁香梅脚踩两条船,现在两条船硬碰硬,一条船把另一条船碰烂了,没法收场了。所以,又恼汹汹地质问梁香梅说:“原先我问你,你追过别人没有,你说没有。我还问你,别人追过你没有?你一口咬定说没有。可是你看,黄料科说你大妈接了他家的四样礼,说我成了搅事的……”
梁香梅急忙辩解,说:“黄料科是个癞皮狗,是他死皮赖脸地纠缠我,我从来没应过他一句话!”
王全天不认同,说:“你没答应,你大妈收了四样礼,就等于你默认了!”
王全天说的是实情,按乡俗女方接了男方的礼,就是认了亲事。梁香梅泛不上话,心里发虚泛潮,她努力镇静自己的情绪,说:“我大妈是我大妈,我是我,我从来没答应,永远也不会答应!”
王全天眼盯着顶棚,不吭声。
梁香梅不甘心地说:“你也应该先问问我呀!连我面都没见,就……”
王全天猛地情绪激动起来:“又是捶头又是拍脚,不写,连命都保不住!我在哪儿去见你?就这,还把我打得连尿尿都疼得不行!”
梁香梅看到,都是因为自己,把王全天弄成现在这样子。她觉得王全天真冤枉,黄料科真可恶,一口恶气堵在喉咙咽不下去,憋得心怒神慌,说:“是我对不起你,把事没处理好。你放心,我一定还你个公道!我就不信了,他黄料科还敢把我抢到他屋里去!”
王全天听梁香梅如是说,知道梁香梅心没变,心里稍微平顺些,但又想到梁双树两口的态度,还有黄料科的不择手段,心里忐忑不安,半天,才说:“咱两个的事,我不为难你了,算了吧!”
梁香梅没有意识到到事情这么复杂,黄料科这么下作,觉得自己成了恶狗嘴里的一块肉,越想越愤怒,顾不得礼貌和形象,跟王全天说了句“你甭管!好好养你的伤!有我哩!”就红着眼,旋风般跑出房子,推上自行车朝外走,和进前门的田彩云碰了个满怀,两人都几乎摔倒。田彩云在拦与不拦的犹豫间,梁香梅出了门,跨上了自行车。
眼看着梁香梅骑上车子走远了,田彩云这才跑进房子,看见气得嗷嗷的王全天,满怀心思地说:“刚才那女娃,是不是你对象?”
王全天沮丧地说:“是的。”
田彩云有点担心地猜测着说:“你对象哭着走了,你俩吵嘴了,是不是因为她看见我给你洗衣服?”
王全天硬气地说:“嫂子,这不关你的事。”
田彩云摇摇头,说:“这梁香梅我听人说过,性子烈得很,敢当女骟匠,是个厉害下家。”
王全天扭着脖子,不说话。
第33章 退礼
梁香梅从王全天家门出来,偏腿跷上自行车,穆桂英踏营一般,冲出巷道,向缑家湾飞去。耳边风声呼呼,脑子里就像有千军万马在驰骋,各种声音,各种念头交迭起伏,一时间只觉得头要爆炸似的。
梁香梅一进家门,把自行车一扔,跑进房子,爬在炕上呜呜地哭。梁双树两口闻声跑进房子,没有问为啥哭,只是站在一边唉声叹气。
就在梁香梅走后不久,邻家张兰就进了门,张兰说:“黄西亮说,天下无媒不成婚,叫我给两个娃娃跑个腿。他叔,他婶,娃小不懂啥胡说,大人可别胡说,你老两口把黄料科家的彩礼接了那么长时间,突然说不愿意就不愿意了?你老两口说是娃不愿意,拿不住娃的事就不接彩礼么!人前一句话,屙出来还能煨进去?你家连个猪圈都没扎,凭啥领养猪补贴?你不愿意把女许给人家,凭啥吸人家的烟,喝人家的酒?就这还没结婚,结了婚,两家变成一家,你家再不会过穷抽筋的日子……”
张兰把梁双树两口连讽刺带挖苦地诉说了一顿,梁双树两口脸烧的像是沾了屎的鞋底打了。心里想着,女儿回来后,一定要商量个了结的办法。梁香梅回来了,只是个哭着,哭得梁双树两口心里发毛,啥话都没法出口。前面给金杏招女婿,招出一大摊子事,刚刚了结,过了没几天安生日子,梁香梅这儿又乱鼓咚咚,唉,这家里成了乱事堂了!
梁香梅哭够了,哭累了,也哭出办法来了。梁香梅起来,擦把脸,喝口水,简洁扼要地给父母把黄料科的所作所为,还有王全天的现状,还有自己的主意说了一遍。父母终于明白,这个黄料科是个不能招惹的主儿,把女儿嫁给她,不是给打死,就是被怕死!于是,一家人重新算计,如何凑钱,如何退礼,如何应对黄料科和黄西亮,一直弄到半夜,才把一切想清楚,弄妥当了。
过了几天,把钱凑够了,梁双树有意识在黄西亮家门前转悠了几回,看黄西亮回来了没有,回来了就把钱退给他。黄西亮没有回来。在转悠的时候,被刚从黄西亮家出来的张兰看见了,张兰把梁双树拉到一边,满脸堆笑说:“胡转悠啥哩?直接进去说就对了,黄西亮不在谷雨在,正等你的话哩,顺手把你女儿的生辰八字给了,让你未来的亲家把两个娃办喜事的日子一定,我这媒人的脸上多风光的。”
梁双树冷着脸,快步走了。张兰脸上的笑容凝固了。
梁双树担心把事再搁出事,第二天一大早,就搭公共汽车,上县去找黄西亮退彩礼了。
车的最后排只有一个空座位,梁双树仄楞着身子,两手捂着挎在胸前的布袋,走了过去。刚坐下,把布袋搁在大腿上,掏钱准备买票,摸遍了身上的几个衣兜,没有找到零钱。梁双树估摸老婆可能把零钱和彩礼钱都装进布袋里了。他解开布袋口取钱,拿出一个手帕裹着的小包,里面是彩礼钱,一塌子零钱用绳子和小包缠在一起。坐在前排的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小伙,装作无意的样子注视着梁双树的举动,给梁双树右边的一个中年妇女说:“阿姨,咱两个换个座位,我跟这位大叔谝一谝。”说着顺手要过梁双树手里的钱,朝前面喊:“给这位大叔买票。”
梁双树接过车票和找的零钱,给小胡子笑。
小胡子贴紧梁双树坐下。梁双树觉得有些挤,挪了挪身子。小胡子掏出两根烟,一根给梁双树,一根自己拿着。掏出打火机要给梁双树点烟,梁双树说:“车上吸烟没地方弹烟灰,不吸。”要把接到手里的烟还给小胡子。小胡子说:“你拿着,过会下了车吸,是好烟,硬中华。”梁双树把烟夹在了耳朵上。
小胡子问:“大叔,你上县办事还是……?”
梁双树看了一眼车窗外移动的田野,说:“到县上找个人。”
一路上,梁双树的心思全在退彩礼上,寻思黄西亮如果答应了结这事,好说,不答应了结呢?对小胡子的问话接一下不接一下,小胡子一看老汉不搭话,也就再不吭声了。
车经过畜牧局门口,梁双树下车,小胡子也跟着下车,一下车,拿出打火机要给梁双树点烟,梁双树连忙推挡,说:“不吸不吸,你忙你的,我还急着寻人哩。”
梁双树来到畜牧局门口,探头探脑往进走,没想刚踏进门,就被门卫挡住了:“哎哎,老汉!你找谁?”
“我找黄西亮。”梁双树不解地说,“你挡我做啥?”
门卫板着脸问:“你是黄局长的啥人?”
梁双树瞪着眼,说:“一个村里的,他把我叫哥哩。咋咧?”
门卫笑着说:“不咋不咋,黄局长下乡去了,事紧不紧?事紧了,我给你打电话联系。事不紧了,你明天来,他肯定在。”
“事紧。”梁双树说。
门卫去办公室打电话联系去了。
梁双树在畜牧局的院子转悠,等黄西亮回来。
院子本来不大,办公大楼正在施工,整个院子变成了一个建筑工地。水泥搅拌机轰隆隆,震得人耳朵很不舒服,工人们戴着着安全帽在忙碌着。梁双树看见一个开升降机的工人在吸烟,想起了自己耳朵上还夹着一根好烟,取下来在鼻子底下闻了闻,走到吸烟的工人跟前,笑着说:“借个火。”吸烟地工人把烟递了,梁双树点了烟,把烟还了,深深的吸了一口,吐出烟圈,再深深吸了一口,吸第三口的时候,突然失去知觉,昏倒在了地上。
开升降机的工人吓了一跳,大声喊:“快来人,人昏倒了。”周围正在干活的工人听到喊声,以为出事故了,撂下手中的工具,跑了过来,一看,不是工队上的工人,就问开升降机的工人咋回事。开升降机的工人把过程一说,大家一边把梁双树扶起坐在地上,一边议论这人是不是突发心脏病或脑溢血病,有人急不择言,喊:“叫兽医!叫兽医!”
城关兽医站和县畜牧局在一个院子办公,对面房子的兽医听到喊声来了,问明情况,摸摸脉搏,翻翻眼皮,看看舌苔,说:“不像是得病的样子。”兽医过去是人医改学兽医的,闻见鼻孔里的出气有一种自己曾经做手术用过的麻醉药味,看见地上还冒着烟的半截香烟,捡起,搭在鼻子上闻了闻,说:“这根烟恐怕有问题。”
兽医让工人们把梁双树抬到树底下,弄了个湿水毛巾给梁双树擦额颅,一会会功夫,梁双树清醒过来,问这么多人围着自己弄啥。兽医拿着半截烟说:“你刚才突然昏倒在地上了,你吸的这根烟是哪儿来的?”
梁双树把烟的来历说了。
兽医说:“怪不得哩,这烟丝是用麻醉药水处理过的,是小偷偷人时用的。”
梁双树如梦初醒,找来自己的布袋,布袋底下被割了好几个口子,好在口子不大,钱包没有漏出来。梁双树出了一身冷汗,如果真的让小偷得手了,空手见黄西亮,不把人丢大了!
畜牧局院子的一切恢复正常。
黄西亮下乡回来进局里大门的时候,当着满院子的人,拉住梁双树的手,笑着说:“是你?走,到我的办公室。”
黄西亮见了梁双树的热情程度,大大出乎梁双树的预料。梁双树悬在半空的心落了地。
黄西亮胳膊窝夹着黑色皮夹,领着梁双树边往里面的三间平房走去,一进办公室,黄西亮把皮夹往桌子上一扔,把外套脱了,搭在旁边的衣架上,掸掸裤子上粘的尘土和草叶,在脸盆里洗了个手,倒茶递烟。黄西亮指指面前的木凳子,让梁双树坐了,自己坐在了凳子对面办公桌的沙发上。
办公桌是宽大气派的老板桌,棕红色桌面,油光发亮。桌面摆放了一沓文件材料,一部电话,一个高级玻璃茶杯,茶杯里的茶叶像松针一样在淡绿色的茶水中漂浮。沙发是棕红色皮质沙发,黄西亮一坐下,整个身子陷进沙发里,两手搭在扶手上,靠背高出人一头。梁双树觉得自己比黄西亮矮了一截,怪不得人都把头削尖当领导哩,人往这地方一坐,势多大的,笨狗也变成狼狗了!
黄西亮没有寒酸一句,单刀直入地问:“咱两个住在一个村子,隔三见五就能碰上一面,啥事把你急得跑到县上来找我?”
梁双树的手不自觉地在捏弄着布袋,说:“还不是两个娃的婚事。”
黄西亮说:“两个娃的婚事好着哩么,只等结婚了,还有啥说的?”
黄西亮的口气,让梁双树突然感觉黄西亮的态度,和刚才在院子见了自己的热情态度不一样了,内心一阵恐慌,心里有点乱了,话说的有些不浑全了:“你的家好……好家,料科也……好娃,如果咱两家当亲,我家肯定不会……不会吃大亏。”一急把“不会吃亏”说成“不会吃大亏”。
黄西亮飘出来一句:“小亏也不会吃。”
“对,没有吃的亏,只有沾的光。”
黄西亮话头一转,说:“照你这么说:你是跟我商量两个娃结婚的事来了?”
梁双树满脸涨红,说:“我给你回话来了,退彩礼来了。”说着从包里掏出手帕包裹的钱,搁在桌子上,接着说:“这总共是三千二百元,两千元的彩礼、烟酒折算的钱,领的养猪补贴,全都算在里头了,如果不够,我再想办法。”
黄西亮的眼睛盯着梁双树的眼睛,一句话也不说。
梁双树说:“为这事的,女儿哭闹,老婆憋气,我左右为难,家都不像家的样子了。你就看在咱两个从小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份上,饶了我吧,接了我退的彩礼,权当没有这回事。”
黄西亮半天没说话,眼珠子盯着梁双树乱转。过了半支烟功夫,才哼哼着,沉声说道:“强扭的瓜不甜,实在不行就算了。我倒无所谓,就怕我儿子狗东西不听我的。”
梁双树听了,急切地说:“那咋办?”
黄西亮阴阴地一笑,说:“还能咋办?我给他做工作么。”说着走到办公室门口,探身门外,两边望了望,把门关了,示意梁双树过来。
梁双树走到黄西亮跟前。
黄西亮说:“有人举报我给你家发养猪补贴的事,县纪检委要派人调查,你帮我个忙。”
梁双树不解地问:“我把领的养猪补贴退给你,你退回去,不就完了?我能帮你啥忙?”
黄西亮说:“事情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。”黄西亮打着手势,嘴搭在梁双树的耳朵上,嘀嘀咕咕了一阵。
梁双树听了难为情地说:“这能把人哄过去?”
“这你就不用管了,你按我说的来就行。我给你说的这事,你不能给任何人说,包括你老婆和你女儿,说了传出去,我落个对抗组织调查名,丢了乌纱帽,你也说不过去。”
梁双树眼瞪大了,还想争辩。
黄西亮说:“这事又不花你一分钱,下个苦的事,有啥难为情的?”
梁双树擦擦额头上的虚汗,说:“不难为情,不难为情。”
第34章 偷猪粪
梁双树在县城连一口饭也没吃,就去汽车站搭车。
走到汽车站门口,看见一摊人围着看热闹,走过去一看,是那个给他烟的小胡子和另个一个小黄毛,在打一个老汉,一边打还一边骂:“谁偷你钱来?老狗日的胡说啥哩!”那个老汉和梁双树年龄差不多,被打得在地上翻滚,可是拉住小胡子的衣服襟不丢手,一个劲地喊:“那是我给娃看病的钱,你把钱还给我!”
梁双树一看是小胡子,心里陡然升起一股怒气,这狗日的,差点把我的钱偷了去,现在又偷了人家给娃看病的钱!脑子一热,冲上前去,一拳照着小胡子的脸面打上去,小胡子猛不防被打得身子一踉,鼻血流了下来。梁双树一把抓住小胡子的手,说:“把钱给老汉,要不打死你!”那个小黄毛一看梁双树打了小胡子,朝着梁双树屁股就是一脚,梁双树差点跌倒,但手却不松,反手狠劲一拧,把小胡子拧的疼得大叫,旁边看热闹的人也大喊助威:“把钱给老汉,啥钱都偷!往死里打!”小胡子和那个小黄毛一看起了众怒,只好把钱包丢给那个老汉,梁双树手一松,小胡子和小黄毛小伙一溜烟跑了。
那个丢钱的老汉拿着失而复得的钱包,感激地要对梁双树磕头作揖,梁双树赶忙扶起,说:“这狗日的早上给我迷魂烟,差点把我的钱偷了!”周围人说:“老汉快走,小心小偷叫人来报复!”梁双树忍着屁股上的疼痛,赶紧上了车,坐在靠窗的座位上。
车驶出了县城。梁双树心里轻松了,一者终于把礼退了,二者车已经离开县城,小偷把人叫来也没用了。心一轻松,这才四下里乱看,看见车上的人都看他的手,低头一看,手里还攥着那个被小偷割破的烂布袋。原来装钱的布袋几个口子连在一块儿了,小口子变成大口子了,用不成了,梁双树想了想,一把把烂布袋扔出了窗外,也省得老婆子见了问,问了骂。
梁双树一进门,老婆何秀珍和女儿梁香梅围上来。见梁双树手里空着,没把装钱的布袋拿回来,估摸事情有眉目。
梁香梅没有问,去倒水了。
“黄西亮把彩礼接了?”何秀珍问。
梁双树“嗯”了一声。
何秀珍揪着围裙的手松开了。
梁香梅把水杯往父亲手里塞,父亲没接,说:“先做饭,一天没吃,心里寡得不想喝水。”
何秀珍责怪说:“你是石头人,吃个饭影响啥事了。爱吃羊肉泡,几年了再没吃过,到县里了,也不吃。”
梁双树没有接何秀珍的话。
过了会儿,梁香梅端来了两个馍和一碗稀饭,炒的鸡蛋、青辣子。
梁双树吃饭的时候,眼睛时不时往后院里瞅。
何秀珍往梁双树瞅的地方看了一下,墙角搁了一堆烂砖头,说:“你吃饭哩,一个劲地看烂砖头,吃烂砖头呀?”
梁双树胡乱地刨了两口饭,手在嘴上一抹,走进了后院,把砖头踢了几脚,说:“把铁锨给我拿来。”
何秀珍问:“你要铁锨弄啥?”
梁双树说:“你拿进来我给你说。”
何秀珍拿铁锨往后院走。
梁双树接过铁锨在墙角铲了起来,说:“扎猪圈。”
何秀珍疑疑惑惑,问:“咱又不养猪,你扎猪圈圈你呀?”
梁双树说:“你不说话,我不会把你当哑巴,不该问的甭问。”
何秀珍大声说:“香梅,你大一回县上的中魔了,不养猪扎猪圈哩。”
梁香梅走到父亲跟前,说:“大,你……”
梁双树不容梁香梅开口:“想帮忙了,给我提水端砖和泥,不想帮忙了,离远些。闲话少问。”
何秀珍给女儿说:“香梅,走,你跟妈到房子去,别理老神经。”
母女俩走出了后院。
梁双树一个人,又是提水和泥,又是砌砖,哼呲哼呲扎开了猪圈。
母女俩好气又好笑。
梁香梅见帮不上忙,车子一骑,到养猪场去了。
梁双树从后半天一直干到天黑,像模像样的猪圈扎成了,拍拍身上的土,拉着架子车,架子车上搭了前后挡板,拿着锨出了门,好大工夫没有回来。何秀珍正疑惑,梁双树拉着满满一架子车猪粪回来了。何秀珍捂着鼻子把架子车辕往后一扭,骂:“人家把猪粪往出拉,你把猪粪往进拉,你成猪脑子了?”
梁双树不吭声,把何秀珍推开,把猪粪拉了进到了后院,“咵”地把架子车辕一丢,说:“你没说错,我不是猪脑子,能把猪粪拉回来?”
正说着,张兰进来,高喉咙大嗓子喊:“哎,梁双树,得是你刚在村外的粪堆上拉了一架子车猪粪?”
梁双树翻了一眼张兰:“是你家的?”
“不是我家的,我问你是闲得嘴痒了?黄西亮真是的,让你没养猪领养猪补贴,把你闻猪粪味耽搁了,偷开猪粪了。”
梁双树听了“偷”字,觉得人格受了侮辱,说:“我刚装猪粪的时候,碰见你男人邱来了,他没吭声,说明他同意,你还上门骂骂咧咧。”
“我男人是泥捏的泥性人,人把他妈背去他都不管,早都不理家里的事了,他有啥权随便把猪粪给你?”
梁双树心里清楚,张兰的气没在一架子车猪粪上,而在瞎了的黄料科和梁香梅的婚事上。她是借机出气。梁双树还招无术,心里憋屈。他走到后院,拿起锨,把倒在猪圈里的猪粪狠狠地拍打,猪粪四处飞溅。
何秀珍上前拦挡,抓住锨把,说:“你这是弄啥么?”
张兰说:“羞先人么弄啥哩!自己没本事,拿猪粪出气,怪猪粪的屁事!”
梁双树蹲在地上,两手抱头,把头埋得很低。
何秀珍歪还没发完,说:“你溅了一身的猪屎,今晚就睡在猪圈里,不要进房子。”
晚上,何秀珍梁香梅都睡了一觉了,梁双树还蹲在那儿。
梁金杏去后院上厕所,没上成,打了个转,出来了。
何秀珍披着衣服,跑进后院,说:“金杏要上厕所了,你还跟死猪一样蹲在那儿,把娃憋死呀?”
梁双树这才要起来。由于蹲的时间长了,猛地往起一站,头昏目眩,摔倒在了地上。何秀珍和梁香梅跟梁金杏听见人倒地的声音,跑出来扶他。梁双树已经爬起来坐在了地上,执拗地不让母女仨搭手。
月亮昏晕,星光稀疏,村庄在熟睡中,唯独梁双树家的后院里,一个人坐在地上,何秀珍和梁香梅、梁金杏站在旁边。一家人个个的心里都苦苦的,疼疼的,像被虫子咬了。
偷猪粪引来风波,惹得老婆何秀珍甚至怀疑梁双树去县上找黄西亮退彩礼,和黄西亮说的不好,有气憋在肚子里,该不会是脑子受了刺激,神经耍麻达了?
天还没亮,何秀珍就悄悄摸黑穿衣服,惊动了身旁熟睡的梁香梅。
梁香梅问:“妈,你起来这早干啥么?”
何秀珍嘴贴在梁香梅的耳朵上,说:“邻村有个医生,看神经病看得好得很,我叫给你大看一下。”
梁香梅转了个身,揉揉惺忪的眼睛,说:“你见风就是雨,没事寻事。”梁香梅不愿意让母亲去找医生。
何秀珍边扣衣扣边说:“家里有个神经病,日子就没法过。你没看东头虎子的大有精神病,把锅端的搁在巷道中间,给锅里尿尿,说搭醋哩……”
梁香梅说:“你再不要说了,要去你去。”
何秀珍叫了梁金杏作伴,母女俩可怜兮兮地披着晨曦,踏着晨露,吹着晨风,找治神经病的医生去了。
日上三竿,何秀珍和梁金杏叫看神经病的医生还没有回来,一辆小车停在梁双树家门口。
车上下来三个人,走进了梁双树的家门。
“你……你是弄啥的?”正在扫地的梁香梅问。
“这是梁双树的家吗?”领头的人开了腔。
梁香梅说:“是的。”梁香梅向里屋喊:“大,有人找你。”
这时,何秀珍和梁金杏,还有那个叫来看精神病的医生到了门口,看见门前停了一个小车,何秀珍不知道出啥事了。医生说:“你都要把病人送到大医院去呀,还叫我弄啥?”何秀珍一把拉住医生,说:“不是,不是。叫我看,一大早,哪儿来的小车。”两人都疑疑惑惑没理站在腰门口说话的几个人,向门里走去。
梁双树听见梁香梅说有人找,从里屋走了出来。
领头的人问:“你是梁双树?”
领头的人说:“我们是县纪检委的,走,领我们看一下你养猪的地方。”
梁双树把三个人准备领到后院去看,刚走到后院门口,领头的人站住了脚,给另外两个人说:“好了,猪圈里太臭了,在这儿看一下就行了,你两个看,哪不是猪圈么!梁双树养猪了,走,回。”
三个人走了。
何秀珍问:“你死老汉唱得是哪出戏?”
梁双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老婆的问话,看着身旁的医生发愣,何秀珍说,是她请来医生给他看看,是不是脑子受吃亏了。梁双树赶紧跟那个医生说,没事没事,自己只是头晕,现在好了。然后,给了医生五块钱,让医生走了。
梁香梅母女仨跟着梁双树进了门,问事情经过,梁双树牛起来了,说:“我是猪脑子,你还问我哩?黄西亮说有人举报咱家没养猪领养猪补贴,通过这事想把他扳倒,县纪检委要调查,叫我回来扎个猪圈,借几架子车猪粪,做做样子。调查这事的人是他的铁哥们,只要有个猪圈,猪圈里有猪粪就行。如果问养的猪咋了,就说猪得猛病死了。把他家的,调查的人连猪圈跟前都没去,哎,世事该瞎哩。”
何秀珍说:“那你为啥不给我和香梅说?我看把你气成神经病了。”
梁双树说:“黄西亮专门叮咛,谁都不能说,说的出了事,跟我搁不下。再说,你的嘴跟蒸馍的烂笼一样,一圆圈跑气,我敢给你说?”
梁香梅说:“黄西亮父子两个人交不过,给他帮的这忙弄啥么?”
梁双树说:“你瓜娃些,黄西亮早都给你大把圈套设下了,说不帮他过这个坎,他不了结你和他儿子的婚事。”正说着,嘶地一声,屁股疼起来了。
梁香梅赶紧问:“大,你这是咋咧?”
梁双树把自己差点被迷晕,后来在车站上打小偷等详说了一遍,听得何秀珍母女三人心惊胆颤,又为梁双树的为那个老汉讨回钱包而高兴。梁香梅说:“大,没想到你还是个见义勇为的老英雄!”
梁双树高兴得笑了,觉得自己在黄西亮面前丢尽的自尊,在老婆和女儿面前找回来了。